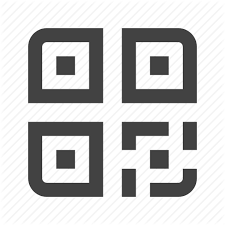武松提刀归来那日,清河县大雪。 他本欲直奔县衙,告发嫂嫂与西门庆通奸毒兄之罪,可脚却在嫂嫂门前停住了——门缝里漏出一点橘红烛火,像极了当年嫂嫂递热汤时那双含笑的眼。
他推门而入。
潘金莲正对着铜镜卸钗,乌发瀑布般倾泻,雪色中衣半褪,露出肩头一抹蔷薇膏色。她听见动静,回头,唇角先勾起笑,再慢慢绽开,声音软得像化开的蜜:“二叔,你回来了。”
武松的刀“当啷”坠地。
雪光从破窗灌进来,照得她肌肤胜雪,锁骨处一粒朱砂痣像新滴的血。那双眼,似嗔似怨,似喜似泣,勾魂摄魄。
“你回来了?”她轻声问,泪珠却先滚下来,挂在睫毛上颤巍巍,像随时要跌进他心里。
武松喉结滚动,声音哑得不成调:“你毒的。”
潘金莲不答,只缓缓起身,衣襟滑落更多,腰肢在烛影里扭出一道惊心动魄的弧。她走近,每一步都踩在他心跳上。
“二叔,你恨我。”她停在他面前,呼吸喷在他颈侧,带着兰麝香,“可你看,我这双手——”
她抬起手,指尖沾着胭脂,轻轻覆上他胸口,“当年给你缝虎皮坎肩的,也是这双手。”
武松猛地抓住她手腕,青筋暴起。
他想掐死她。
可指尖触到她脉搏,一下一下,像小兽撞他心门。她的眼泪终于落下,烫在他虎口。
“武二,”她忽然贴近,唇几乎擦过他耳垂,“你哥活着时,我夜夜独守空房。你漂泊在外,可知我多想……多想有个人,像你这样高大,像你这样——”
她声音哽咽,却伸手解他衣带,“能护着我。”
“住手!”武松低吼,刀鞘滚落在脚边,发出闷响。
可他没推开她。
潘金莲的指尖像蛇,滑进他衣襟,贴着他滚烫的胸膛画圈。她踮脚,唇贴上他喉结,轻声道:“杀我啊……杀了你嫂嫂,你夜里做梦,还能梦见谁?”
武松的理智在那一瞬崩断。
他听见自己心跳如擂鼓,血往头顶涌,眼前只剩她湿漉漉的眼、微张的唇、雪白颈窝里那粒诱命的朱砂。
他猛地扣住她后脑,吻下去,像溺水者抓住最后一根浮木。
那一夜,雪落无声。
武大郎的灵位在堂前冷冷注视,烛火却在里屋燃得正旺。
天将亮时,潘金莲蜷在武松怀里,指尖描他胸口旧伤疤,声音软得像猫:“二郎,我们走吧。清河待不下去了,官府会捉我们……去梁山,好不好?”
武松盯着帐顶,胸腔里翻江倒海。
杀兄之仇、通奸之罪、江湖道义……像无数把刀剐他心。
可她贴着他,温香软玉,呼吸拂过他颈窝,像春水化开冰。
他终于开口,声音低得像叹息:“……好。”
三日后,清河县传出风声:武大郎暴毙,弟武松携寡嫂连夜潜逃,行踪不明。
西门庆悬赏千金,官府画影图形。
可谁也没想到,景阳冈的打虎英雄,已在嫂嫂一滴泪、一声叹里彻底沉沦。
梁山泊,水天一色。宋江闻武松上山,大喜,设宴洗尘。席间,武松醉卧,潘金莲独坐湖边,抚着琴弦,唱一曲《皂旗白》:
“哥哥死了无人问,嫂嫂随你上梁山。 若教官府来捉我,刀下夫妻不分散。”
歌声袅袅,传入武松耳中。他猛地睁眼,月光下,潘金莲回眸,笑意里带着挑衅与柔情。
那一刻,武松知道,自己再回不去清河了。